主持人語:
[學人檔案]欄目楊東諭圍繞著關于“氣韻生動”概念的釋讀,撰文介紹在國際美術史界以六法、南北宗、山水畫研究著稱的日本美術史論家田中豐藏。——徐翎
田中豐藏(Tanaka Toyozo,1881—1948)20世紀日本重要的美術史學者,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中國文學專業,師從瀧精一深研中國古代美術理論,具備扎實的中國美術史論基礎與出色的中文語言能力。
田中通過對中文語義的辨析及中國古代美術理論的重新闡釋,糾正了當時日本學界將日語和漢語當做同類型語言進行讀解研究的誤區〔1〕;尤其是對南北宗論命題和六法論體系的研究,不僅在日本和海外藝術學界產生廣泛影響,也為當時中國文人畫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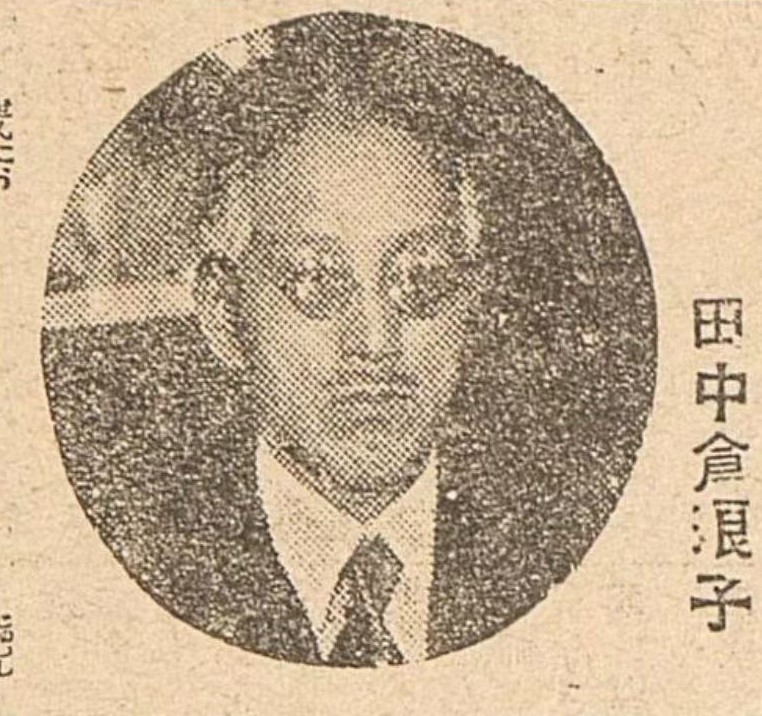
田中豐藏(Tanaka Toyozo),1881.10~1948.04,號倉浪子、倉瑯子、滄瑯子
田中關于南北宗論的研究先后發表于1912年《國華》第262號到281號,后組成《南畫新論》并收錄于1964年出版的《中國美術之研究》一書。雷德候(Lothar Ledderose)指出,田中豐藏立足于中國山水畫藝術風格的分析,重構了中國古代美術史發展的時空序列,其明確晚明為南北宗論形成時間節點的觀點引發了對中國繪畫史既有書寫范式的重新思考〔2〕。田中豐藏明確南北宗畫派形式格律的特征,即北宗尚“骨法”,重視畫面的骨骼和力感;南宗尚“氣韻”(stimmungsmaleriei),著力于以動態畫面抒寫主觀和直覺性的思想感情。1903年日本學者岡倉天心在《東方的理想》一書中釋讀“氣韻生動”為“活躍于宇宙間的偉大氣韻”〔3〕,是以繪畫線條形式的韻律去表現抽象美感;岡倉天心對“氣韻生動”的理解啟發了西方藝術學界對這一命題的關注與譯介。邵宏指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中國繪畫藝術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中對“氣韻生動”命題的譯介,顯然受到岡倉天心的影響,翟理斯在岡倉天心譯介前兩法的基礎上完整翻譯了“六法”,且持續影響到夏德(Friedrich Hirth)、卜士禮(Stephen W. Bushell)、賓庸(Laurence Binyon)、福開森(John C. Ferguson)和喜龍仁(Osvald Sirén)等海外漢學家〔4〕。

田中豐藏《中國美術の研究》,1964年二玄社出版
圍繞“氣韻生動”命題的理解在日本藝術學界形成三種主要觀點:大村西崖、金原省吾和伊勢專一郎以內感的音響和韻律理解“氣韻生動”,青木正兒立足詩畫共通明確“氣韻生動”是文人畫的古拙趣味,瀧精一和坂西志保將“氣韻生動”理解為精神基調和生命律動〔5〕。應該說,大村西崖和金原省吾以西方寫實藝術的線條律動來理解中國核心藝術概念的主張,基本反映了19世紀中期之后西方立體派、抽象派等近代美術思潮傳入的影響,并且啟發了早期中國現代美學家滕固、豐子愷等人立足跨文化交流視閾互釋互鑒中西藝術理論命題,“氣韻生動”與“感情移入”的對比闡釋就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6〕。在20世紀上半葉,“有節奏的生命”(Rhythmic vitality)成為日本及海外藝術學界對“氣韻生動”的主要闡釋模式〔7〕。這種闡釋以西方審美心理學為參照系,將對“氣韻生動”的理解限定于“節奏”(Rhythm),實際上反映了一種脫離中國古代美術發展史實的闡釋傾向。青木正兒、田中豐藏等人均以共時性的比較研究釋讀“氣韻生動”命題,或從文人畫的歷史發展抽繹出“氣韻”為畫家個性的古拙趣味;或從中國古代美術與美術史的關聯中提煉“氣韻生動”為南宗畫的第一要義,揭示中國畫的本體價值就是藝術作品的生命躍動及感染力。瓊·斯坦利-貝克(Joan Stanley-Baker)認為日本學者對于中國藝術的研究極富方法論的啟示,田中豐藏及其學生島田修二郎顯然受益于德國藝術風格學派的影響〔8〕。區別于大村西崖《文人畫的復興》(1921年)和金原省吾《中國上代畫論研究》(1924年)立足西方線條形式抽象化理解“氣韻生動”命題,田中豐藏在《南畫新論》(1912年)、《有關氣韻生動》(1913年)、《宋畫的特質》(1918年)、《六法之意義》(1922年)、《中國美術思想》(1936年)、《美術鑒賞的態度》(1946年)等一系列文章中〔9〕,以“氣韻生動”命題為中心形成了基于中國畫本體價值的理論詮釋,其理論研究的“前驅性與開創性”〔10〕對當時乃至當下中國藝術觀念史研究和全球美術史的范式重構具有一定的啟示價值。本文基于近年來海外藝術學界重新書寫“全球美術史”的問題導向〔11〕,以田中豐藏對“氣韻生動”命題的專題性研究為基礎,剖析田中豐藏以宏觀的畫史研究和微觀的考據學相結合的美術思想研究脈絡,及以藝術學與美術學的交融構筑的關于中國美術思想研究的藝術理念與詮釋范式。
一、中國畫的本體價值:由“骨法”而導出的“氣韻”
日本近現代美術的發展主要受到中國文人畫的影響,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言道:“18世紀的日本藝術家非常崇拜中國文人畫,稱之為‘南畫(nanga)’。這些中國文人繪畫通常畫法簡略,筆觸敏感,即景生情,與詩歌和文人傳統緊密相關,強調對個人情感和敏感性的表達,不注重對客觀世界的準確描繪。”〔12〕“南畫”概念在中國畫學語境和日本畫學語境中的意義是不同的:中國古代畫學典籍中的“南畫”概念主要指涉地域形貌所造就的繪畫藝術風格,其次也可視為是對中國古代“南宗畫”的略稱〔13〕。據徐小虎考證,日本“南畫”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18世紀中國晚明作品和清代畫譜傳入日本萬福寺之后,創寺先驅祇園南海等人將中國畫學觀念、技巧融入日本藝術文化所形成的一種新繪畫表現樣式〔14〕。也即,“南畫”是日本特有的概念,亦是以“氣韻生動”“寫意”“逸”為審美追求。田中豐藏以中文語義原境為研究基礎,以中國古代畫論與史料文獻為實證依據,以日本近現代收藏的中國畫為詮釋范本,系統生成了理解中國畫“真性”的獨特觀點,呈現了日本藝術學界對中國繪畫本體的多維闡釋。
日本藝術學界對謝赫“六法”的關注可追溯至19世紀末岡倉天心對日本新型繪畫——“日本畫”的推崇。值得指出的是,1910年左右在大村西崖、瀧精一和田中豐藏等人的引導下,日本藝術學界掀起了以現代西方學術方法研究東洋美術的熱潮,有論者提出此時期日本藝術批評界對于南宗畫個體情感因素的重視,實際上可視為對當時歐洲表現主義興起的一個有力的亞洲回應〔15〕。加之此時期日本南畫的發展面臨內部創新和外部歐化浪潮的雙重困境,這也形成了內藤湖南、田中豐藏等人研究南宗畫審美趣味的現實動因〔16〕。1927年田中豐藏自歐洲游學后,在東西繪畫傳統的對比中提出:“中國的或者說東洋的,以毛筆勾畫出來的墨線和礦植物顏料呈現在縑帛或紙上的畫,總給人一種質樸和謙遜的感覺,和西洋古往今來的畫比起來,中國畫是非常平面的、圖形化的、裝飾性的以及非現實的。”〔17〕據此,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畫以體驗的復雜性構筑其在世界精神文化中的價值,因而繪畫所再現的對象并不僅僅訴諸于觀者的視覺,而是經由視覺推動了觀眾更深層次的精神作用,其魅力即在于以精神體驗的深刻性來補充表現的平面性。如何以現代文藝理論話語體系概說和論述中國古代美術的發展歷程和核心命題,實際上成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日學者所共同面對的難題〔18〕。田中豐藏基于東洋藝術文化的觀念和思考方式,認為中國畫本體價值在于對個體形態美的超越,由“骨法”而導出的“氣韻”凝結了中國畫主觀、直覺和非現實的特質。
1.畫的“輪廓線”:“骨法”釋義
在田中豐藏看來,“氣韻”與“骨法”實為不即不離的辯證關系。他對“骨法”與“氣韻”的結構辨析集中于《六法之意義》(1922年)和《中國美術思想》(1936年)兩篇著述中。田中認為,王充《論衡》的“骨相說”可視為《古畫品錄》的“骨法”概念的思想源流,六法中“骨法”原是由指涉個體面相衍化而出的,“骨法”從文論到畫論的衍化反映泛論面相形態到繪制對象體形輪廓的過程。王充《論衡·骨相篇》以“表候”謂“骨法”,提出“論命者如此之于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于身形定矣”〔19〕是在漢代氣化宇宙論的思維下視人體骨相身形為自然之氣的凝定,“骨”也成為了人的命理氣運、福禍寵辱的顯化方式。魏晉人物品藻中的“骨”轉向了審美性,成為人物精神風貌、性情品格的評價標準。顧愷之的“骨法”首先用以論證“以形寫神”,又從文學中轉化為人物的“風骨”。謝赫的“骨法”正是繼承了顧愷之,因此田中將其理解為“畫的輪廓線”,即日本的“描骨”。
田中豐藏提出在近代西洋畫中,畫家主要運用色彩和光線的綜合來呈現物象的三維立體效果,但在西洋版畫中的審美體驗觀眾無法感知到“骨法”。中國畫的線條忠實于對象的原始輪廓,畫家以流動運轉的線條來呈現物象的立體,《女史箴圖》作為存世最早的絹畫具有重要的白描特質,白描即反映了畫家以“骨法”對物象原本形態的把握〔20〕。瀧精一在《顧愷之畫的研究》一文中言“氣韻”應當為六朝畫家真意的凝結,他提出:“最吸引眼球的便是畫中多處淋漓盡致地描繪了人物或動物的表情動作。《女史箴》首段中,馮媛擋熊之時,所有人都被描繪得十分細致。而成帝坐輦行進時,擔輦之人處所繪更為精細……可謂是巧造情勢,即為得到氣韻而作出的努力。”〔21〕田中豐藏提出由“骨法”形成的畫面反映中國畫“主觀、直覺和非現實的特色”〔22〕,這一界定立足于魏晉時期繪畫藝術的發展史實,且從主客融合出發以畫面自足性與畫家主觀意識來抽繹“骨法”含義,由“骨法”至“氣韻”的釋讀路徑反映其重視藝術概念所蘊含的情感價值。
田中豐藏認為“氣韻”生成于涵括畫家情感的動態畫面,由“骨法”所形成的“氣韻”來源于畫家主觀品味,因而“氣韻”反映了畫家精神世界的思想深度,并且“骨法”和“氣韻”呈現畫家天賦中尚意和尚情的分界,“骨法”為畫家意志的集中,“氣韻”則動態表現畫家的情感。古原宏伸認為《南畫新論》實際為田中豐藏研究中國繪畫史最為卓越的論著,原因在于:“田中在文章中尖銳地批判了董其昌‘南北宗論’存在的矛盾。他的這種批判早于世界上的任何學者,比1935年青木對‘南北宗論’的批評更為徹底。”〔23〕田中豐藏指出以“南北宗”論山水畫的發展,實際上反映藝術創作中筆法技巧與思想情感的割裂,明清時期南宗畫的獨勝來源于文人畫家對思想與情感的重視,由“骨法”至“氣韻”的生成體現了中國古代山水畫的本真性,畫家的創作得以超越于物象的基本形體,成為中國畫獨特價值的集中體現。
2.“六法”原意的探求:“骨法”融于“氣韻”
“氣韻”作為精神要素居于六法的首位,但田中豐藏認為“氣韻”原意的探求“要完全脫離開那些附加的意義”〔24〕,顧愷之《論畫》中的“神奇”“天趣”會通于六法之首“氣韻”,唐末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同樣提出“氣韻”不可比附“臺閣樹石”和“車輿器物”〔25〕,但田中豐藏認為“氣韻生動”適用于所有類同山水的靈性對象,且寫物象之真僅為繪畫的初步要求,“應物象形”和“隨類賦彩”不能引發觸動心靈的力感,因而“‘氣韻’與‘寫實’(應物象形、隨類賦彩)是相對的,它要求畫面之上要有靈感”〔26〕。
田中豐藏認為相較郭若虛“氣韻生知論”,張彥遠將“氣韻”“骨法”與“寫實”并列的解釋更切合謝赫原意,“寫實”“筆法”和“氣韻”統一于畫家的“用筆”,“氣韻”來源于寫實并超越于具體畫面,凝聚了藝術作品的本體價值。張彥遠以書畫同體的視角明確藝術創作中主體立意的重要性,田中豐藏據此提出書畫藝術是相互提攜促進的。基于中國古代書畫藝術從同源而異流的發展脈絡,田中豐藏明確書畫藝術同樣重視主體的人格教養,“骨法”通過“用筆”融于“氣韻”,獲得了超然象外的意味。但田中豐藏將張彥遠的六法解釋視為謝赫原意的切實理解,此認知并不符合中國古代畫論的發展事實。《歷代名畫記》成書年代約為9世紀中期,是唐代人物畫和宗教畫蓬勃發展的時期,畫家重以運筆的線條滲透生意與情感。張彥遠在《論畫六法》中賦予“骨法用筆”以超越形式層面的精神價值,即“骨法”是畫面的筆墨結構與物象之“真”,是把握對象內在本質與精神的途徑。這實現了對“骨法用筆”的創新性解釋, 賦予了筆墨、線條以精神層面的意蘊。因而田中豐藏對“六法”理論史的理解存在著片面之處,但他較完整地把握了不同門類藝術的發展脈絡和書畫同源而異流的演進機制,在書論史和畫論史的結合中考察書法與繪畫不同藝術交互影響對“六法”理論史演變的具體作用,剖析促成“骨法用筆”和“氣韻生動”觀念意義發展和嬗變的外因,其整體詮釋思路乃是基于六朝至唐書畫藝術的演進歷程去還原“骨法”與“氣韻”的結構序列。
二、“氣韻生動”:藝術作品的生命躍動及其感染力
除了東西繪畫的互鑒與六法的結構序列,藝術本體維度也構成田中豐藏對“氣韻生動”命題的重要釋讀方向。溯源中國古代大文論視閾下“氣韻生動”命題意義的生成過程,創作論和品鑒論成為歷代畫論家釋讀“氣韻生動”命題的主要維度,由此漸趨形成圍繞中國繪畫藝術本質的多維解釋。在1912年發表的《南畫新論》一文中,田中豐藏立足于由唐宋至明清畫學典籍的排列分析,釋讀“氣韻”(stimmungsmaleriei)為“氣氛”(mood)、“影調”(stimmung)和“細微差別”(nuance)的綜合,揭示“氣韻”賦予了藝術作品以生命的意義。以“氣氛”理解“氣韻”,作為古代畫學概念的“氣韻”能夠超越描述藝術作品審美特征的場域,在現代文化語境中指向了一種藝術形象與感知者所共同在場的審美體驗。在1913年發表的《有關氣韻生動》一文中,田中豐藏提出“氣韻生動”命題自提出后在歷代畫論得到連續討論,并將“氣韻生動”視為中國畫最高評判標準和東方美學理想目標:“我對于中國畫評人沒有簡單地把美和愉悅,而是把‘氣韻生動’作為繪畫的第一要義,感到非常高興和感謝。作者賦予物象的生命,強烈、深刻地跳躍在畫面上。繪畫所能表達的內容至此得以完成。藝術不是概念,更不是形式,而是‘氣韻生動’。”〔27〕他從藝術門類互通的維度拓展了“氣韻”概念的適用范圍,指出“氣韻”應適用于所有的藝術,將《古畫品錄》后歷代畫論對“氣韻”概念的解釋分為“真實的生命表現”“人格修養的反映”和“用墨的濃淡與光澤”三類,基于“氣”范疇和“韻”范疇的原義推演去詮解“氣韻生動”命題的藝術意蘊。
1.生命流動與品格風姿:“氣”與“韻”的原義及衍化
首先,田中豐藏重新分析了“氣”范疇的意義,指出中國早期氣論思想散見于先秦著作。《管子》《莊子》和《呂氏春秋》中多見“云氣”,“氣”范疇原指一種流動狀態的本原物質。田中豐藏指出先秦氣論的“勇氣”“才氣”是“氣”的衍化概念,將“氣”與個體心靈相聯系,賦予了“氣”以道德觀念層面的特質。《莊子·知北游》所載的“通天下一氣耳”〔28〕主導了中國古代氣論思想的發展,“一氣”是將“氣”視為萬物之形的基礎,將自然世界視為連貫統一的整體性存在。晉人王羲之《記白云先生書訣》有言:“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29〕清人朱履貞《書學捷要》提及:“一氣貫注,筆致俱存。”〔30〕“一氣”的聚集和運轉構生了主體與對象互感的有機整體。中國古代書畫論中的“一氣”是對哲學元范疇“氣”的發展深化,是化生自然萬物的基礎元素和本原。田中豐藏認為郭若虛將“氣韻”觀念的意義擴展到無生命物的物體,宋以后呈現畫家創造力的人物畫、山水畫皆反映了活躍而有韻律的強烈生命力。
其次,田中豐藏指出《玉篇》以聲音的和諧釋“韻”,“韻”的現代通義為“詩的韻腳”〔31〕。六朝時期人物品藻的盛行,賦予了“韻”以審美意義。錢鐘書《管錐編》提出:“釋韻為聲外之余音遺響, 足征人物風貌與藝事風格之‘韻’,本取譬于聲音之道。”〔32〕“韻”范疇的聲學意義可視為是六朝時期其藝術美學意義衍生的基石。且“韻”的原義為“介于某個音程中間的和聲”〔33〕會通于節奏、韻律和音響。“韻”范疇在六朝典籍中衍化為“大韻”“韻宇”“雅韻”等概念,總體而言都是以“韻”喻指人的品格風姿,是經由觀者的審美經驗去感知對象的生命本真。《世說新語》《文選》《宋書》《晉書》以“韻”喻指個體的內在性情、品格氣度,向內肯定和凸顯個體的自我價值,體現了魏晉時期藝術精神文化的自覺。依田中豐藏的觀點,謝赫在品評繪畫中聯和“氣”“韻”,并將“氣韻”置于“比著色、寫形及用筆等更高的位置”〔34〕,是不以道德和感覺的美感來作為品評繪畫的最高標準。“氣韻生動”以“應物象形”為基礎,但“氣韻”的生成來源于物我交感的精神共鳴,因而能夠超越象形表達更為純粹的寫實意蘊。
2.“氣韻生動”意義的歷史流變:三種代表性解釋
明清中國文人畫家將“氣韻生動”視為山水畫第一要義,但田中豐藏強調南宗畫第一要義的“氣韻生動”其實與謝赫的原意相差極大,相對而言張彥遠和荊浩的“氣韻”解釋更契合謝赫原意。他認為“氣韻”的形成不可離于“形似”,二者是不即不離的關系。荊浩在《筆法記》中區分了繪畫中的“真”與“似”,即言繪畫的真實是“氣”與“質”的兼備,無“氣”則無精神,無“質”則不能顯現對象的本體〔35〕。郭若虛的“氣韻生知論”受到宋代理學和道德論的主導影響,立足于內省式的“氣韻”解釋,是重在以畫家人格論“氣韻”的高低,顯然不同于《古畫品錄》中的“氣韻”之義。
通過張彥遠、荊浩和郭若虛的對“氣韻”的遞進解讀,“氣韻”與“形似”“氣象”等藝術命題發生了多維聯結。那么歷代審美意識的嬗變如何影響“氣韻”概念的意義轉向?作為畫學最高審美理想的“氣韻”是如何以筆墨語言被具象化的?按照田中豐藏的理解,宋代文人“內省式”的氣韻觀影響到清代畫論,形成了第三種代表性解釋——“自于技巧的氣韻觀”〔36〕,因為后兩種解釋均將畫家個體的人格修養視為“氣韻生動”形成的關鍵,但基于技巧層面的“氣韻”解釋“大多是基于空洞概念上的一種心情,離實際切身體會和反思相差甚遠”〔37〕。田中豐藏揭示基于筆墨技巧層面的“氣韻觀”,實際上反映了繪畫創作中藝術主體和物象的分離。宋元之后繪畫筆墨語言的程式化發展傾向,反而助推了基于技巧層面的“氣韻觀”成為明清南宗畫家的主要理論,“認為如實描繪自然景物太過平庸,所以故意畫出遠離寫實物象的畸形作品,并稱之有氣韻。把筆端的小技巧,當作是‘氣韻生動’”〔38〕,即是說明清南宗畫家以筆墨技巧釋氣韻,對象生命精神的呈現是經由“形似”“傳神”而達到“氣韻生動”,元人夏文彥《圖繪寶鑒》所言“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寫人真者則能得其精神”〔39〕。據此,田中豐藏指出《圖繪寶鑒》以“傳神”釋“氣韻生動”是對概念的正確理解,“藝術要表達的不是對象物的客觀存在,而是其生命。對象物的生命即作者的生命”〔40〕。綜以言之,田中豐藏對“氣韻生動”命題的分類解釋立足于中國美術與中國美術史的發展史實,突出了“生機盎然地躍動”對于藝術創造的意義,明確宋代理學思想與南宗畫派審美趣味對“氣韻”意義嬗變的作用。但他將“氣韻生動”的意義進行了絕對化的擴展,將“氣韻生動”命題視為古今中外藝術作品的最高要求,反映了一種混淆東西方藝術理想、審美趣味的認知模式。他以“氣韻生動”為中西詩歌、書法、繪畫及戲曲等不同藝術的共同目標,呈現了簡單化、片面化的解釋思維。因田中豐藏重視藝術家生命力的創造,將藝術個體視為物象的造物主,認為藝術個體賦予了對象的生命,導致他將藝術創作的本源完全歸于藝術主體的創造力,未能具體區分中國古代藝術與藝術本體的關系。
三、從“氣韻生知”到“氣韻不可學”:基于文人畫和南宗畫的分析
田中豐藏對于“氣韻生動”的現代釋讀不僅立足于畫論重要觀點的分析,更深入到文人畫和南宗畫的創作理念和藝術價值層面。應該說藝術作品所呈現的自然觀指涉了南宗畫與北宗畫的本質差異,直指兩種思潮在中國古代山水畫史中的交替融合、主導。宋代之后的畫論始以主觀、內省、參禪的維度解釋“氣韻生動”,宋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提出:“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41〕即認為“氣韻”的生成需經由藝術個體嚴格的內省功夫,畫家呈現藝術的本真必須要脫卻氣質之俗,詩意的追求、自娛的意境、以書入畫和非寫實的筆墨為宋畫的重要特征。田中豐藏并沒有止步于對歷代畫論的詮釋,而更進一步明確了南北分宗的根本意義。他揭示文人畫、南宗畫的不朽價值來源于對“氣韻生動”的追求,以元四家為代表的南宗畫家立足于“自然本位”的創作思想,在藝術實踐中向內發掘了詩意與心靈哲學。“氣韻生動”是藝術的終極目的,更是藝術主體“整個生命隨描寫物一起迸發出來的靈感”〔42〕。
1.舍皮相以喚氣韻:圍繞徐熙落墨畫法的考察
徐熙、黃筌的花鳥畫體現了五代至宋初花鳥畫藝術形態的成熟。在田中豐藏看來,相較于黃筌重筆墨之法而輕描繪色彩的徐熙花鳥畫的“氣韻”是中國畫的真正追求。基于徐熙真跡畫本今已無存,《圖畫見聞志》《夢溪筆談》和《圣朝名畫評》成為田中豐藏勾勒徐熙藝術作品形態的主要史料。《圖畫見聞志》載其“學窮造化,意出古今”〔43〕,《夢溪筆談》有述徐熙墨法“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44〕,劉道醇《圣朝名畫評》評徐熙畫法“形似”與“氣骨”兼備,不以形態和色彩為表現的中心,而獨重描繪花果的“神韻”和“氣韻”。依田中豐藏的觀點,徐熙落墨畫法的最大特點即是輕視模仿、脫于色彩,僅運用單色水墨實現生意、自然和氣韻的有機結合,其畫法的核心在于真實再現自然以抒發“野逸”趣味。徐熙的花果寫生凝結了宋畫的基本特征,如《宣和畫譜》所載“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氣風神,為古今之絕筆”〔45〕。田中豐藏對徐熙繪畫精神的研究首先基于史料,其次更以傳牧溪的《芙蓉圖》進行佐證研究,從中明確盈尺小幀的花鳥畫同樣能以靜寫動,進而在落筆自然中抒發出不亞于巨幅山水的心靈底蘊。
2.“氣韻生動”的萌生:南宗畫的第一要義
立足于中國古代山水畫的發展史實,田中豐藏認為文人畫與南宗畫是包含與延展的關系,“南宋四家”和“元季四家”為北宗畫和南宗畫的代表,在審美趣味和藝術形式上的不同取徑反映二者的本質差異。南宗畫以詩趣和自然為本位,以“氣韻”的生成作為繪畫的終極追求,“元季四家”的藝術創作凝結了最徹底純粹的南宗畫形態。“元季四家”主師法董源、巨然,倪瓚的創作以高度的自省精神脫離前代“縱橫習氣”,南宗畫家的“游戲藝術”是以“非寫實”的精神抒發個體對自然的印象、感覺,可理解為“印象”或“詩趣”,指向“氣韻生動”的萌生。并且,田中豐藏以“氣韻”為“南畫的第一要義”“最重要的至純精髓”〔46〕,亦為“藝術的終極目的”〔47〕。北宗李思訓開創金碧山水的畫法,擅以筆力遒勁和綿密線條表現山水之姿,色澤典雅勻凈,風格峻峭富麗,富有裝飾意味,為“筋骨之畫”而非“精神之畫”,發展至宋元趙幹、趙伯駒、趙伯骕等人,墨守成規使藝術風格趨于形式化和平面化。
綜以言之,南北宗繪畫的差異并非限于技巧層面,北宗繪畫是“筋肉之畫”,從李思訓、李昭道的金碧山水到“南唐四家”的蒼勁筆力,多以運筆剛健、形式和諧契合北禪的“漸悟”,但典型固化的宏大構圖、缺乏思想意蘊造就了圖像的空洞化;南宗繪畫則為“氣氛之畫”,其藝術呈現專注唯我和主觀,以詩人的純真之眼描繪自然的生機和趣味,因而“和空洞的北宗畫相比,無疑更加接近自己的感覺和自己的內部生命”〔48〕。由此,田中豐藏以近代思維明確了南宗繪畫的藝術價值,在中國繪畫思想史的發展中辨明南北二宗畫派的基本特點——經由史學文獻、畫學文獻的考證辨析,田中豐藏結合藝術實踐與理論詮釋南北二宗在藝術風格、繪畫技法、審美追求的差異,凸顯作為南宗畫神髓的“氣韻生動”在南宗山水畫史中的重要價值,賦予“南北宗論”命題以繪畫史學和繪畫美學的雙重價值;對前代將唐代視為南北宗形成時期的觀點進行了辨正,指出“南北宗”是后世根據明代董其昌等畫論家的分類所形成的理論命題,更循南北兩種思潮的演變軌跡探究了中國古代山水畫史發展的思想動因。田中豐藏以“氣韻生動”作為南宗畫的至純精髓,不僅契合中國南宗繪畫藝術風格、作品意蘊的歷時性演變過程,更體現了基于中國南宗山水畫史發展歷程的宏觀把握。
結語
田中豐藏在緊密聯合中國古代美術實踐和美術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畫的本體價值是藝術作品的生命躍動及感染力,并以此闡釋以“氣韻生動”為神髓的中國古代山水畫論。將田中豐藏對“氣韻生動”的研究置于西方沖動型、寫實模仿型美術思潮泛濫的日本美術現代化進程,我們便可以理解田中豐藏對“氣韻生動”的理論研究更體現了一種基于東方文化本位的堅守,樹立了一種基于中國畫本體的觀念和思考方式,進而立足于近代中日美術跨文化交流的視角,明確以元四家為代表的中國南宗畫以靈感、精神等關鍵要素促進了日本近世南畫的發展和嬗變,例如江戶時代池大雅、與謝蕪村和柳澤淇園等人的南畫創作皆不同程度取徑于中國古代南宗畫。值得注意的是,在田中所處的那個時代,日本學界并未將中國與日本分為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而是作為對抗西洋美術存在的東洋美術來看待,即南畫是“日本與中國=東洋”的精粹,《南畫新論》是對其作出的符合日本文化自信的“近代化”定義〔49〕。總體而言,田中豐藏基于宏觀的史學結構對中國畫本體價值展開抽繹性研究,凸顯了東方繪畫區別于西方繪畫的審美趣味與藝術價值。
田中豐藏主要著述目錄:
1.《東洋美術談叢》,朝日新聞社1949年出版。
2.《日本美術之研究》,二玄社1960年出版。
3.《中國美術之研究》,二玄社1964年出版;賈佳、龔辰譯,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出版。
4.《天平雕刻》(與兒島喜久雄、高村光太郎、志賀直哉合編),小山書店1954年出版。
注釋:
〔1〕[日] 古原宏伸《日本近八十年來的中國繪畫史研究》,《新美術》1994年第1期。
〔2〕德國藝術史學界雷德候在2021年6月30日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舉辦的講座《改變東亞美術史領域的四篇二十世紀博士論文》(Four path breaking 20th century theses)中提出,田中豐藏在《南畫新論》中對中國南北宗論的駁斥應是受到了德國藝術史風格學學派研究模式的影響,此后中國現代學者例如滕固、顧頡剛、童書業等人開始運用風格學、考古學、社會學和圖像學等方法重新辨析中國古代山水畫史中的“南北宗論”命題。
〔3〕[日] 岡倉天心著,蔡春華譯《中國的美術及其他》,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3頁。
〔4〕邵宏《東西美術互釋考》,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214—215頁。
〔5〕邵宏《“美術”入華與英譯“六法”》,《美術觀察》2020年第2期,第57—58頁。
〔6〕李雷《“氣韻生動”與“感情移入”》,《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7〕李雷《20世紀上半期“氣韻生動”概念的跨語際實踐》,《文藝研究》2021年第2期。
〔8〕Joan Stanley-Baker, Chūgoku kaigashi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IIa (Southern Song, Liao and Jin), Ars Orientalis, Vol.17 (1987): 187-191.
〔9〕[日] 田中豐藏著,賈佳、龔辰譯《中國美術之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版,第 465—473頁。
〔10〕陳振濂《近代中日繪畫史交流比較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版,第253頁。
〔11〕2015年巫鴻教授受葛兆光教授邀請,在復旦大學舉辦的“光華人文杰出學者講座”中提出“全球美術史”的范式重構應該以歷史個案作為研究基石,“全球美術史”的歷史性就在于以時間和地域作為主要維度去分析美術的發展史實,進一步還原和發掘不同文化和藝術傳統的交流過程。參見巫鴻《全球景觀中的中國古代藝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5頁。
〔12〕[英] 邁克爾·蘇立文著,趙瀟譯《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頁。
〔13〕王洪偉《民國畫壇“南畫”一詞淵源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3年第1期。
〔14〕徐小虎著,劉智遠譯《南畫的形成:中國文人畫東傳日本初期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頁。
〔15〕Mikiko Hirayama, From Art without Borders to Art for the Nation: Japanist Painting by Dokuritsu Bijutsu Kyōkai during the 1930s,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65, No. 2 (2010): 357-395.
〔16〕王洪偉《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對“南畫”研究的貢獻》,《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17〕同〔9〕,第1頁。
〔18〕張哲俊主編《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東亞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85頁。
〔19〕王充《論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頁。
〔20〕同〔9〕,第3—4頁。
〔21〕[日] 瀧精一著,吳玲譯《文人畫概論》,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版,第 90頁。
〔22〕同〔9〕,第3頁。
〔23〕[日] 古原宏伸《日本近八十年來的中國繪畫史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編《中國美術史學研究》(朵云67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頁。
〔24〕同〔9〕,第26頁。
〔25〕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
〔26〕同〔9〕,第26頁。
〔27〕同〔9〕,第96頁。
〔28〕郭慶藩撰,王孝魚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33頁。
〔29〕王羲之《記白云先生書訣》,載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第37頁。
〔30〕朱履貞《書學捷要》,載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第607頁。
〔31〕同〔9〕,第98頁。
〔32〕錢鐘書《管錐編》(第4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364頁。
〔33〕同〔9〕,第92頁。
〔34〕同〔9〕,第99頁。
〔35〕荊浩《筆法記》,載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一),第6頁。
〔36〕同〔9〕,第89頁。
〔37〕同〔9〕,第90頁。
〔38〕同〔9〕,第91頁。
〔39〕夏文彥《圖繪寶鑒》,載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二),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第847頁。
〔40〕同〔9〕,第95頁。
〔41〕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載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一),第468頁。
〔42〕同〔9〕,第76頁。
〔43〕同〔41〕,第483頁。
〔44〕沈括著,劉伯嚴、樊凌云譯《夢溪筆談》,團結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頁。
〔45〕俞劍華注譯《宣和畫譜》,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頁。
〔46〕同〔9〕,第80頁。
〔47〕同〔9〕,第76頁。
〔48〕同〔9〕,第79頁。
〔49〕[日] 千葉慶《美術史學と帝國主義:田中豊蔵「南畫新論」》(における見出されたもの/見逃されたもの),《美學》2002年53卷3號,第72頁。
本人作者:楊東諭,北京語言大學藝術學院講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發表在《美術觀察》2022年第4期。
(圖、文:博士生 楊東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