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022首屆物質文化與設計研究青年學者優秀論文評議結果公布,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博士研究生周少華(指導教師:藝術史論系副教授 陳彥姝)論文《明代云南雕漆再考》榮獲第一組工藝美術史研究一等獎。
《明代云南雕漆再考》
在明代雕漆產區中,云南當年可能地位重要,前輩學人曾提出,明代雕漆有兩個地區系統,一是嘉興,另一就是云南。可惜,因為文獻史料稀少、作品不易確認,且在今日云南已難覓當年遺存遺跡,此前的探討不夠細密深入,云南雕漆的問題一直撲朔迷離、難以澄清,就明代漆藝乃至工藝美術研究而言,不得不說是個遺憾。本文即著眼于這一研究薄弱之處,試圖通過縷析核心文獻,結合相關作品,進一步揭示云南雕漆的歷史面貌,并期拋磚引玉、求教方家。
一、文獻再檢視
已知直接述及云南雕漆的文獻集中于元明時代的鑒藏類著述,今見最早的介紹出自王佐(主要活動于15世紀上中葉)增補的《新增格古要論》:
剔紅器皿,無新舊,但看朱厚色鮮,紅潤堅重者為好,剔劍環香草者尤佳。……今云南大理府人,專工作此,然偽者多。南京貴戚多有此物,有一等通朱紅,有一等帶黑色,好者絕高,偽者亦多,宜仔細辨之。[1]
假剔紅,用灰團起,外用朱漆漆之,故曰堆紅,但作劍環及香草者多,不甚值錢。又曰罩紅,今云南大理府多有之。[2]
王佐校增曹昭(活躍于元末明初)《格古要論》,起于明景泰七年(1456)四月,迄于同年七月,后在天順三年(1459)付梓,以上記述反映的最可能是明代前期情形。文中說,云南大理府人善造剔紅,但其中假的不少,假剔紅用灰團起堆花,常飾劍環、香草紋樣,價格低廉,而據原文標題,假剔紅即“堆紅”。
到弘治(1488-1505)末年,宋詡(約活動于15世紀下半葉至16世紀上半葉)關于云南漆器品種、紋樣的說法出現幾點變化:
雕漆。云南造,多花草,有棱角,無劍環,不及剔紅黑者渾厚圓滑。……
累漆。云南作,似滑地西皮,其漆乃煮過者為之,器亦堅固。今徽州以漆面為花,制尤堅久。一種堆紅者,則累漆之贗也。[3]
宋詡仍說云南造“雕漆”,但紋樣無劍環,且提到了作品多棱角、不渾厚,已知的材料里,這是首次,只是他將雕漆與剔紅、剔黑并列,認識與今天不同。下條又記,云南也造累漆,而堆紅是累漆之贗,這與《新增格古要論》堆紅是假剔紅之說抵牾。
到晚明,高濂(約活動于嘉靖至萬歷間,即1522-1620年前后)對明代云南雕漆風貌的描述更加豐富具體:
……(雕漆)民間亦有造者,用黑居多,工致精美,但幾架、盤、盒、春撞各物有之,若四五寸香盒以至寸許者絕少。云南以此為業,奈用刀不善藏鋒,又不磨熟棱角,雕法雖細,用漆不堅,舊者尚有可取,今則不足觀矣。有偽造者,礬朱堆起雕鏤,以朱漆蓋覆二次,用愚隸家,不可不辯。……[4]
高濂稱云南剔紅不善藏鋒、不磨熟棱角,與宋詡的描述一致,此外又補充說“雕法雖細,用漆不堅”。他也提及偽造的剔紅,由所述工藝推敲,當與《新增格古要論》相合。
在品種、風格之外,晚明的沈德符(1578-1642)在云南漆藝史的梳理上有所貢獻: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1403-1424)、宣德(1426-1435)間所謂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埒,間有漆光暗而刻文拙者,眾口賤之,謂為舊云南,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是說,辨難蜂起。予曰:總之皆云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以去,由是云南漆織諸技,甲于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滇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為郡縣,滇工布滿內府,今御用監、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后漸以銷滅,嘉靖間又敕云南揀選送京應用,若得舊云南,又加果園廠數倍矣。諸骨董默不能對。[5]
據沈氏所言,云南漆作興起的基礎,是唐代中葉大理國破成都后擄掠的百工。持相似觀點的另有李日華(1565-1635),他說,“髹剔銀銅,雕鈿諸器,滇南者最佳”,認為這固然有“地饒精鐵、沙石、璣貝,易于綴飾”的原因,更要緊的在于“唐時酋王閣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流傳有法”[6]。關于云南漆作的肇始,這是兩份珍貴的意見。而對本文,沈德符有關元明時代的縷述更有意義:明代云南平定,當地漆工進入內府,服務宮廷,此后逐漸消亡,嘉靖間(1522-1566)又命云南揀選送用。他還提到,當時有些古董家對云南雕漆的印象大致是漆光暗淡、刻紋樸拙。
二、年代、品種與風貌考辨
討論明代的云南漆器,以上幾則材料最為關鍵,在另外一些文獻,如王三聘(1501-1577)《古今事物考》,劉侗(1593-1636)、于奕正(1597-1636)《帝京景物略》,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識》中,也能見到與之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字,但它們當系承襲抄錄,實際并無新意、乏善可陳。上引材料提供的知識已經不少,但說法有時很模棱,意見有時不統一,與遺存的實物也不能完滿對證。若結合其他材料,則以下幾個問題還可繼續探討。
1. 年代
沈德符說,云南漆工明初布滿內府,嵇若昕循此記載,經由表征分析,指出山東鄒城明魯荒王朱檀(1370-1390)墓出土的剔黃筆管應系明初滇工之作[7]。推測即使屬實,此例也為孤證,云南派漆作在明初的發展脈絡仍然太過朦朧。相比之下,如今對于明中期的知識稍多,關于曾任職云南的官員應履平(?-1453)的一段記載至為珍貴:
應履平,字錫祥,奉化人。……升貴州按察使,奉敕同兵部尚書王驥、平蠻將軍蔣福帥師征麓川,有功,升云南左布政使。時有太監奉命監造剔漆器皿進用,供費百出,民不能堪。平諗其將訖工,別造私物,密疏欽造數完,或且止,或加造,奉旨:“畢造,起送部”。檄至,履平懷之,中道馳入,太監怒叱之,對曰:“奉旨,請回京”,出文以視,遂解一方倒懸。……[8]
“剔漆”顯系雕漆。按《明英宗實錄》,應履平升任云南左布政使在正統三年(1438)七月[9],則在此之前,云南已有太監在奉命監造雕漆進用。北京與云南之間,千里迢迢,跋涉艱險,器用傳辦、送交實在不易。聯系沈德符的說法,依常理推想,倘若宮中仍有云南漆工,則應該不必去當地造辦,倘若宮中曾有云南漆工,則到此時恐怕已消亡殆盡。另外還可注意的是,英宗皇帝(1436-1449[年號正統]、1457-1464[年號天順]在位)年少登極,到正統三年,也不過十二歲,在位之初,太皇太后張氏臨朝,“三楊”等勛舊輔政,朝野尚稱清晏,且按照當年士大夫集團的政治品格,造作的旨令如經外朝傳下,一定會遭到極力的勸阻。對于此事,最易產生的推測有兩個。一是它系此前宣德年間的遺留。但在明代,每逢新帝即位,總要與民更始,即位詔中,循例要下令停止各項采辦和造作,若有監督內官,也要從速回京。宣德時派造而正統初未停,以及停后重啟,現在都沒有史料證明。另一個推測是,這確實是正統朝派下的造作,不過它并非出自外朝動議,而是源于內府的主張,或者是由內府徑直將旨意傳達到地方。在明代中期,這類操作有事例可尋。
弘治五年(1492),宮中命陜、甘二處織造彩妝絨毼曳撒數百事,引來了監察官員的諫阻,依奏議所言,旨令的下達系由司禮監傳寫帖子,而外朝的工部未曾經手。文中還推測,皇帝之所以這樣操作,可能是因為心有不安[10]。盡管這則記載的時間較晚,但仍有參考價值,正統初年令云南供用雕漆器皿,或許也是有此心理、走的這條路徑。于此,還可考慮的是正統朝司禮監的一個重要執掌者及其與英宗皇帝的密切關系。此人就是明代幾個擅權干政的大宦官之一——王振(?-1449),英宗即位后,他即掌領司禮監,由于為人黠慧、曾經陪侍青宮,很受皇帝信重。后來的跋扈乖張在早期即有跡象,以至于他險些被太皇太后處死,罪名就是“侍皇帝多不法”[11]。在不法的諸事里,或許就有鼓動年少的皇帝,亂開艱難的造作。
既然云南還能承接派造,則當地民間的漆作此前應有不小的能力,之后,也可能長期維持,弘治三年(1490)八月間的一則奏陳隱約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巡撫云南都御史王詔等奏:故鎮守太監王舉,不遵詔例,造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其物之重大難致,如屏風石床之類,發本處庫藏收貯,金銀器皿镕化之,與寶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戶、工二部備用,其寄養象只,堪充儀衛者解京,不堪者付與近邊土官,令出馬以給驛遞。得旨:并解送來京。[12]
王舉鎮守云南,他造來進貢的漆器相信就是產在當地,很可能包含雕漆。由時代稍前的這些材料分析,沈德符所言嘉靖時云南又受命遣送工匠,大概是實。
2. 品種


圖1 明中期 滇南王松造
剔紅文會圖方形委角盤
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弘治 尹祿造
剔黑花鳥大盤
原日本私人藏
取自保利藝術博物館編:
《宋元明清漆器特展》,頁69
幾條文獻都說,云南造雕漆,這無可懷疑,出自滇工之手的剔紅現在還有保存,學界多已熟知,即北京故宮博物院那面“滇南王松造”的文會圖方盤。(圖1)上引文獻還幾次提到云南多作摹仿剔紅的堆紅、罩紅,做法是以礬朱、灰團堆起花紋,然后罩漆。《髹飾錄》對堆紅工藝的記述與此大同小異,王世襄先生進一步解釋說,剔紅表里一致,堆紅則里外用料不同,剔紅刻后刀法盡在,堆紅則刻后罩漆,花紋不免臃腫,較難生動流暢[13]。按宋詡和高濂的文意,云南雕漆起碼還包括剔黑。而今,相信為滇工作品的剔黑也有披露,如原為日本私人收藏的一面花鳥紋圓盤,其邊緣有刻銘“弘治年滇南尹祿造”[14]。(圖2)據悉,藏于日本的明代剔黑中,還有些未退光、未打磨、外底較粗糙的作品,它們被通稱為“云南雕”[15]。名稱容易令人將之視為云南雕漆,但事實如何,仍然成謎。
《宋氏家規部》稱,云南所造的累漆近似“滑地西皮”,這說的該是花紋效果。在同卷中,恰也記載了滑地西皮,說“花底如仰瓦光澤,而且堅薄不露素地”。但這個解釋并非原創,它的源頭應在曹昭:
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為貴,底如仰瓦,光澤而堅薄,其色如膠棗色,俗謂之棗兒犀,亦有剔深峻者,次之。……[16]
可見,《宋氏家規部》所稱滑地西皮,實為這里描述的剔犀。由此,依宋詡所說,累漆面貌即近于剔犀。又,“累”與“堆”意義接近,《髹飾錄》對堆漆有記述。按楊明的注解,堆漆有復色之法,指花紋用漆分幾次堆成,每次更換漆色,完成后花紋側面露出有規律的不同色層,很像剔犀。這又正與累漆近似剔犀的說法呼應,看來,累漆極可能就是堆漆。但宋詡還說,堆紅是累漆之贗,在此,他區分真贗的標準想來當與王佐一樣,也是用料,累漆堆花全用漆,而堆紅里用漆灰、在外罩漆。
3. 風貌
作為明代重要的鑒藏著作,《燕閑清賞箋》的意見影響頗大,它對云南剔紅風格的形容曾被數次轉抄。相信就是受了這些文獻的引導,以前見到特征如上述的明代雕漆,專家常常會將它與云南作品聯系,不善藏鋒、用漆不堅,儼然云南雕漆的判定標準。
但明代的云南雕漆應當不只有這種面貌,“滇南王松造”剔紅文會圖方盤就恰好是個證據。王世襄先生早已指出,這只方盤的刀法實屬圓潤一路,風格與宣德朝作品相似,盤邊花卉更是明代早期的做法。由此即知,明代云南雕漆的風貌并不單一,也有明人推重的刀法圓潤的一類。沈德符也認為,“若得舊云南”,可“加果園廠數倍”,依照文意,“舊云南”當系嘉靖間再募滇工以前,即明代早中期的產品。而專家此前正相信,剔紅文會圖方盤的年代應在明中期。總之,云南雕漆應受過嘉興派的影響,有些作品的風格屬圓潤渾厚,在晚明,它們尚能得到文士的認可。按《宋氏家規部》,至遲到其成書的弘治末年,不善藏鋒已成為明人眼中云南雕漆工藝的突出特點。或許在此后的發展中,云南雕漆更多采用新的刀法,終使爽利之風后來居上,圓潤一路退出主流。當然,還該說清,盡管這面文會圖方盤確屬滇工制作,雕刻圓潤渾厚,但它終歸是個孤例,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對其價值,不宜過高估計。

圖3 剔黑花鳥大盤局部
取自保利藝術博物館編:
《宋元明清漆器特展》,頁71
對于認識明代云南雕漆的主流風格,上引近年發表的“弘治年滇南尹祿造”剔黑圓盤相信頗有意義。此盤在紅漆地上滿雕黑漆紋樣,題材為菊花、蓮花、石榴花、梔子花和飛旋、棲息的鳥雀,鳥雀形象甚不醒目,這些花卉是絕對的主體。專家先前已指出,它的漆層較薄,紋飾細部多采用斜刀陰刻,線條流暢縝密而快利。(圖3)比這更易覺察的是,其花紋繁滿細碎,和元明時代嘉興派的圓潤渾厚迥異,而與高濂所言云南的雕法之“細”契合。在沈德符的時代,古董家們非常推重永樂、宣德間嘉興派主導下的官府雕漆,對被認作舊云南的那些則“眾口賤之”,也可見兩類作品風貌必然不同。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文中已經提到云南的“漆光暗而刻文拙”。剔黑圓盤的雕刻其實頗精細考究,難以納入拙的行列,但它滿密細碎的裝飾面貌畢竟與永、宣時代的作品有別,不合于古董家傾心的圓潤渾厚,在中晚明,這個特點或許也曾成為時人眼中云南雕漆的短處,令它們不被愛重。

圖4 明中期 剔紅飛龍紋圓盒
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中期
剔紅穿花龍紋雙耳扁瓶
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中期 剔紅松竹梅草蟲紋圓盒
故宮博物院藏
“弘治年滇南尹祿造”剔黑圓盤或能成為可資比照的標準器,用來分辨可能屬于云南一派的雕漆。因為缺乏可靠的實物對照,以往學者盡管會推測那些用刀露鋒、紋帶棱角的明代雕漆為云南作品,但有時仍要慎重地表示,證據不足,尚待查考。這類器物的典型可舉北京故宮舊藏的一組剔紅,包括碗、盤、盒(圖4)、扁瓶(圖5),主題紋樣有松竹梅、雙龍、雙翼龍、雙螭、雙獅、四獅、盤長靈芝等。一些輔紋非常特殊,如其中一件松竹梅盒上,點綴著蜂、蝶、螳螂、蛙、蜥蜴(圖6),它們極少見于明代官府雕漆,專家稱具有民間鄉土趣味[17]。前人已注意到這組剔紅的刀不藏鋒與文獻相符,而其繁密的構圖、板平的紋樣與這面剔黑圓盤近似,頗能左證它們產在云南,或出于云南漆工之手。


圖7 明中期
剔紅纏枝蓮紋碗
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中期
剔黃纏枝蓮蟠螭紋棋子盒
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中期
剔紅歲寒三友圖圓盤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10 明
剔黑歲寒三友圖委角方盤
安徽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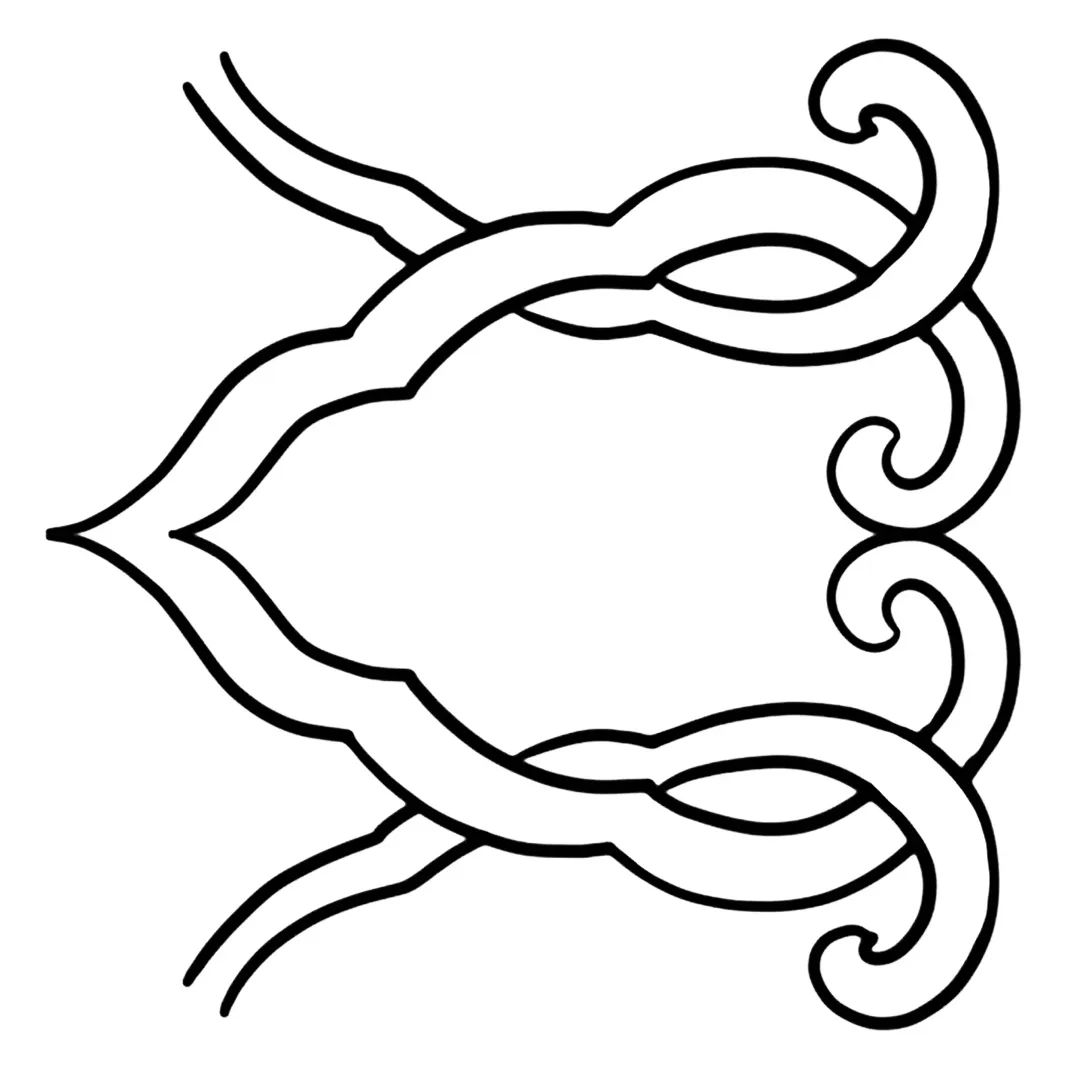
圖11 明中晚期
剔紅松竹梅委角方盤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12 《營造法式》
(故宮殿本書庫鈔本)
劍環紋結構摹繪
綜合參照這些器物雕飾的技法、構圖、題材特征,在已知的明代雕漆中,能進一步推定幾件屬于云南作品,例如此前曾被專家懷疑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剔黑纏枝蓮紋圓盒,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剔紅纏枝蓮紋碗(圖7)、剔黃纏枝蓮蟠螭紋棋子盒。(圖8)另外,還有國博的剔紅歲寒三友圖圓盤(圖9)、安徽博物院的剔黑歲寒三友圖委角方盤(圖10),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剔紅松竹梅委角方盤(圖11),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剔黑牡丹紋圓盒、根津美術館的剔紅獅子牡丹紋圓盒、岡山美術館的剔紅菊花紋圓盒、大和文華館的剔紅麒麟紋長盤[18]等。其中,安徽博物院和大都會博物館兩件方盤的紋樣題材、風格與盤沿的竹節式造型竟幾乎完全相同,區別大致只在漆色,兩者的關系顯然特別緊密,不排除有出于同一作坊乃至同一漆工的可能。

圖13 南宋 銀梅瓶
四川德陽孝泉南宋窖藏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圖14 南宋 剔犀菱花形執鏡盒殘片
福建閩清白樟鄉南宋墓出土
福建省閩清縣文化館藏
最后,關于云南雕漆的紋飾面貌,另有一事需稍加申說。王佐記述,云南的假剔紅多作劍環、香草紋樣,宋詡則稱,云南“雕漆”多花草、無劍環。劍環、香草系指線形紋飾,現在大體確定,要說的是劍環原本的形式與概念。王世襄在批注《髹飾錄》中“剔犀”一節時,以計成(1582-?)《園冶》所附劍環式圈門的圖案,來推測黃成所記的“劍環”樣貌,后繼學者有時也遵從此說。而在今天的海外學界,被認作“劍環”(pommel scrolls)的紋樣,則是中國學人習稱的如意云頭,這一判斷相信得自一些時代較晚的有關中國古兵器的圖示,不為無據。然在《髹飾錄》原文里,劍環與絳環、重圈、回紋、云鉤并舉,雖然都應是線形紋飾,但具體樣式當有不同。又,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論“香合”時提到,“宋剔合色如珊瑚者為上,古有一劍環、二花草、三人物之說”[19],細推文意,似乎劍環之名由來已久。而在北宋李誡《營造法式》的彩畫紋樣中,確實早有“劍環”一名。它整體作對稱多曲狀,一端彎曲斗合,一端聚結出尖(圖12),在當下很多學人那里,這種紋樣也會被稱作如意云頭。建筑裝飾與工藝美術紋樣的相通之處不乏其例,如《營造法式》的彩畫紋樣就多見于宋遼絲綢,裝飾形似劍環紋的銀器曾經出土(圖13),而紋樣相仿的剔犀也已發現了。(圖14)看來,劍環紋的本來面目很可能如同《營造法式》所畫,只不過到后來,它所指代的紋樣或許又有擴展,乃至能夠代表線形紋飾,與花草、人物相提并論。
盡管宋詡稱云南雕漆無劍環,但他所說的雕漆是與剔紅黑器并列的一種,并非今日認為的雕漆,故而不能以此否定王佐的記載。劍環結體簡單,雕刻不難,且據文震亨之言,其地位一度很高,而現在遺存的豐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年制作的繁盛,云南雕漆不做劍環似乎不合情理。還該注意,劍環等線形紋飾多用于剔犀,相信云南的雕漆也包含了這一品種。
三、正德款剔紅圓屏刻銘獻疑

圖15 明正德 柴增造 剔紅人物樓臺圖圓屏 上海博物館藏

圖16 剔紅人物樓臺圖圓屏刻銘
帶正德紀年銘的漆器,長期以來未聞發表。那面“正德丁卯黃陽柴增造”剔紅人物樓臺圖圓屏(圖15)刊布的契機,是上海博物館2018年11月舉辦的“千文萬華——中國歷代漆器藝術”展覽。刻銘的文字為博物館專家釋讀,由圖片分辨,“正德丁卯”“陽”“柴增造”八字較為清晰,沒有疑義,但“黃”字有所模糊,準確與否,還有商榷的余地。(圖16)
參照其他明代雕漆上的刻銘,如“平涼王銘”“平涼王琰”“滇南王松”來看,工匠署名之中的籍貫,一般是府級或以上。然檢索明代地方行政區劃,非但黃陽府遍尋不到,在更低層級的單位中,也沒有符合的地方。故對“黃”字的認讀,或許有誤。此字更可能是“貴”,在字形上,它與圖片所示亦非常相像。而《萬歷貴州通志》所載貴陽府的“方產”之中,明確記有“雕漆器”[20]。雖然這則文獻的時代較晚,但工藝品種極少驟然出現,況且,依方志所載,雕漆造作在貴州并不罕見,說明它在當地應有些傳統,故藉以推斷正德前后貴陽等地出產雕漆,或出過雕漆工匠,應該合情入理。所以,判斷那位柴增出自貴陽并非臆測。而且,從刊布的圖片觀察,這面圓盤的漆色不甚紅亮,較為暗淡,與晚明古董家眼中云南雕漆“漆光暗”的特點似可對應。貴州與云南毗鄰,雕漆風格相信會受其影響,柴增甚至有可能也屬滇工一派。但話說回來,以上只是一種質疑和猜測,銘文究竟是作“黃陽”還是“貴陽”,尚待方家再予嚴謹的辨析與求證。
尾語
在以上討論當中,先行檢視的幾則文獻很受倚重,它們成為考證、分析的基礎。文獻固然珍貴,但局限在所難免,比如鑒藏類書籍的作者不見得熟悉工藝,王佐和宋詡關于假剔紅的認識就產生了分歧。對于倚重這類文獻的危險,本文并非全無意識,之所以仍如此展開,則多緣于史料稀少的無奈。文中依據刻銘器物風格,區辨疑似云南雕漆作品,亦嫌說服力度不足,尚且只能作為猜測。另外,海內外的公私收藏一時難以搜羅齊全,以上援引的實物還不甚豐富,加之筆者不曾從事工藝制作,也沒有機會上手觀摩作品,因而對于實物缺乏直觀認識,寫作僅能藉助文獻記載和實物圖像,解說的深度當然難與漆藝工作者和文博機構學人相比。總之,限于資料和學力,本文的論述一定不免偏頗,甚至多有錯漏。
云南雕漆的問題已困擾學界有年,期待新研究的推出,令其歷史面貌更加清晰,也渴盼新材料的發現,能從根本上解答關于它的眾多困惑。
注釋:
[1]( 明)曹昭編著、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論》(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據清光緒間李錫齡輯刻《惜蔭軒叢書》本),卷8,〈古漆器論·剔紅(后增)〉,頁257。
[2](明)曹昭編著、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論》,卷8,〈古漆器論·堆紅(后增)〉,頁257。[3](明)宋詡,《宋氏家規部》,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6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刻本影印),卷4,〈整備簿籍·長物簿·漆類〉,頁48。[4](明)高濂,《燕閑清賞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據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本雅尚齋刻本),上卷,〈論剔紅倭漆雕刻鑲嵌器皿〉,頁66-67。[5](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據清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卷26,〈玩具·云南雕漆〉,頁661-662。[6](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據民國有正書局石印本),卷3,頁291-292。[7]嵇若昕,〈明初滇工雕漆工藝〉,《故宮文物月刊》,425期(2018.8),頁96-105。[8](明)周希哲修,張時徹纂,《嘉靖寧波府志》(早稻田大學藏,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卷27,〈列傳二·應履平〉,頁37b-38b。嵇若昕先生前曾留意此則材料,并以之簡論云南雕漆貢品,見嵇若昕,〈明初滇工雕漆工藝〉,頁105。[9](明)孫繼宗監修,陳文、彭時總裁,《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卷44,〈正統三年七月丙戌〉,頁851。[10](明)張懋監修,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總裁,《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卷60,《弘治五年二月庚午》,頁1159-1160。[11](清)萬斯同,《明史》,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據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卷405,〈宦官傳·王振〉,頁4995。[12](明)張懋監修,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總裁,《明孝宗實錄》,卷41,〈弘治三年八月庚子〉,頁860。[13](明)黃成撰,楊明注,王世襄解說,《髹飾錄解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據民國十六年紫江朱氏刊本),頁129。[14]保利藝術博物館編,《宋元明清漆器特展》(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2012),頁68-71。[15]李經澤,〈剔黑器概述〉,《中國生漆》,2016年3期,頁13-21。[16](明)曹昭編著、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論》,卷8,〈古漆器論·古犀毗〉,頁256。[17]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65。[18]德川美術館、根津美術館編,《彫漆》(名古屋:德川美術館、東京:根津美術館出版,1984),頁81圖版111,頁82圖版112,頁127圖版181、182,頁296、307、308圖版目錄。[19](明)文震亨,《長物志》(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據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鉛字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卷7,《器具·香合》,頁97。[20](明)王來賢,陳尚象修纂,《萬歷貴州通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日本東京尊經閣藏明萬歷刻本影印),冊18,卷3,〈貴陽府·方產〉,頁64。
本文原刊《故宮文物月刊》463期(2021-10),此次刊發時略有改動。
圖、文來源:工藝美術理論專委會公眾號